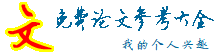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宫震
论文关键词:摘要:产生于蒙古族统治之下的文学样式——元杂剧,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蒙古族文化习俗的一定影响,如称妻子为“大嫂”就是受其“收继婚”习俗影响而体现在杂剧的创作当中的。对于这一点,中山大学的康保成先生曾做过阐述,不过对于他的某些观点,笔者不敢完全赞同,故而在康先生的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再做一简单的探讨
1997年康保成先生在《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上发表了《元杂剧呼妻为“大嫂”与兄弟共妻古俗》一文,对元杂剧中丈夫为何称呼妻子为“大嫂”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认为这与古代兄弟共妻这一习俗有关。但对于康先生其中的某些观点,笔者不敢完全认同,故在此且将自己关于此问题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以求大家指正。
元杂剧中,丈夫对妻子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如“娘子”、“浑家”、“大嫂”、“婆婆”等。称妻子为“娘子”、“浑家”较为常见,也容易为后人理解,但称妻子为“大嫂”或“婆婆”,却很让今人费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类特殊的称谓,作一探究。
据康先生在《元曲选》一百种杂剧的统计中,以呼“大嫂”呼妻的就有二十三种,如:
大嫂,我待要应举走一遭去。(《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楔子周荣祖云)
大嫂,你为甚么跪在这里?(《钱大尹智勘绯衣梦》第三折裴炎云)
家里有个丑媳妇,叫出来见大人。大嫂,你出来拜大人。(《鲁斋郞》楔子李四白)
可见,对妻子以此种称呼,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至于为什么呼妻子为“大嫂”这一原因,康保成在其论文中写到,这是人类兄弟共妻风俗流行的结果。“兄弟共妻”即长兄去世之后,弟弟娶寡嫂为妻的一种古老习俗。
而“兄弟共妻”实则就是在少数民族中间所盛行的“收继婚”,它是蒙古等民族游牧时代一脉相传下来的习俗,是他们进入中原以前的主要婚姻形式。这种颇为奇特的“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隋书·突厥传》)婚姻方式,即父死,儿子可娶后母为妻;兄弟死,其弟可娶寡嫂为妻。史书称之为“妻后母,报寡嫂。”当代人类学家称这种婚姻为“收继婚”。
在宋金元时期,女真、蒙古各族,依然保留着弟娶寡嫂的风俗,虽入主中原,但其风不改。到了元代,“父死可娶其父之妻,惟不可生母耳……兄弟死亦娶兄弟之妻”的收继婚俗一直流行于蒙古族之中,《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谓蒙古族:“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此。”《清稗类钞·婚姻类》云:“盖匈奴之俗,父死娶其后母,兄弟亡收其妻。元人入主中原,其风不改。”并且尤其是南宋以后,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的现象日普遍,在各民族交流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汉族同样也受到了少数民族某些习俗的影响,这当中就包括“兄弟共妻”这一习俗。故在此种情形之下,康保成先生在此文中说:“元人在婚姻问题上比较宋明开放的多。在元杂剧中,少女私奔、寡嫂再醮,妓女从良都不是什么稀奇事。而夫兄弟婚中之‘报嫂’风俗,比之异辈转房制如妻后母、娶寡婶之类,要容易接收得多。”
因此康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既已‘作嫂多年’,其弟以嫂为妻,仍应以‘长嫂’呼之。”“‘视长兄之妻为妻’,就是把大嫂看作妻子,其实此仍是长兄之妻。这种情况,如果在称谓上反映出来,就正与元杂剧中呼妻为‘大嫂’相合。不难推测,其弟以嫂为妻,仍应以‘长嫂’呼之。”
对于康先生的这一结论,笔者还是比较认同的,因为在相关的元杂剧中就提到过兄弟可以娶自己的大嫂为妻,如在马致远的《马丹阳三度任风子》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小叔云:“说的是,哥哥,你若休了嫂嫂,我就收了罢!”
由此可见,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这种“收继婚”习俗,对当时汉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进而体现在元杂剧中就是丈夫称呼妻子为“大嫂”。
但除此之外,康先生还认为,在“元杂剧中,‘大嫂’是对妻子的专称。……而对已婚妇女的敬称,则用‘嫂子’,或在‘大嫂’前冠以姓氏,如张大嫂、李大嫂等,以示与‘大嫂’呼妻有别。”
对于康先生这个观点,笔者很是不赞同,因为笔者在阅读元杂剧文本的过程中发现,在元杂剧当中,还存在着奸夫称呼姘头为“大嫂”的情况,如在《勘头巾》中,刘平远员外之妻与太清庵王道士有染,唆使王将刘杀死,王云:“我杀了刘员外也,拿着这芝麻罗头巾减银环子,回大嫂话去来。”对于这一情况,康先生认为,这也是“报嫂”制的遗迹,但笔者却无法从中窥出所谓“报嫂”制的痕迹。
而对这种呼情妇为“大嫂”的情况,康先生认为“这说明呼妻为‘大嫂’绝非从弟称。”但笔者在白朴的《墙头马上》当中却发现了称别人妻子为“大嫂”的情况,而此处女子绝非姘头或情妇:
“院公云:相公不合烦恼,合欢喜……老汉买羊去,大嫂(指李千金)请房里去者。”
此处,院公只是一个仆人,却呼其女主李千金为“大嫂”,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之前院公称裴少俊为“哥哥”:
院公云:“哥哥(指裴少俊),一岁使长百岁奴,这宅中谁敢提起个李字。”
故此处院公称李千金为“大嫂”,就是——从弟称——对李千金的一种尊称而已。
此外,在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中,也有称别人妻子为大嫂的的记载:
李逵云:“不知什么人将大嫂(指孔目妻)拐的去了。……谁想那哥(指孔目)正告在了拐了俺大嫂的白衙内根前,如今把哥下在死囚牢里。”
这里李逵之所以称孔目妻为大嫂,原因也正在于他将孔目当作了自己了“哥哥”,这一点在文中表现的非常明白,在此不做赘述。
在《墙头马上》一剧中,我们从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将院公当作是裴少俊的弟弟,而兄弟本就应当称其兄之妻为“大嫂”,这本是无可非议的。而康先生在此处却似乎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他在论述兄弟在娶兄之妻为妻后,说“作嫂多年,其弟以嫂为妻,仍应以‘长嫂’呼之。”这里他故意将其写为“长嫂”而非“大嫂”,而实际上“长嫂”和“大嫂”本来就没有多大区别,况且如果按照康先生的观点,此处院公称李千金当为“裴大嫂”,以示与呼妻“大嫂”有别,可是白朴在文章当中却并没有如此书写。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的说明,笔者认为在此处称他人妻子为“大嫂”就是一种“从弟称”,而不是如康保成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元杂剧中,“大嫂”只能是丈夫对于妻子的一种专称或不是从弟称。
故笔者认为,在元杂剧中,呼妻为“大嫂”的情况是受了蒙古等少数民族“收继婚”的影响,但也并不是完全如康保成先生所说的那样,“大嫂”一词仅仅是限于丈夫对妻子的专称,而实际上还应当适应于丈夫的兄弟,呼妻为“大嫂”也当是一种从弟称。同时,我们还必须具体事件具体对待,对于呼妻为“大嫂”,我们一定要考察它所处的语境,而不能妄下结论,如在郑廷玉的《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中:“和尚云:‘大嫂(指张善友妻),你怎么要赖我的?’”此处这样的称呼,就是对一般已婚妇女的尊称,而没有其它具体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晓清.元代收继婚制述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