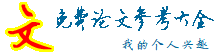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他开枪自杀了,流出来的血是热的,脑浆则是白的,“像没点好卤的豆腐,糊里糊涂的”,因为“这辈子没闹明白的事太多”。[4]
这样一个草莽“英雄”,至死没去思索究竟是革命至上、还是人性人道至上等等。即便如赵刚者,也只是在痛苦的思索, “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或是罪行在党内刚刚露头时,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最终是害人也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5]最后的“亮剑”也只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亮剑》的反思意义。
《历史的天空》无论是写国民党,还是写共产党,都没有回避实写内部的矛盾,尤其可贵的是作家在写这些矛盾时,不是就矛盾而矛盾地展开故事,而是从内部各个关键人物的人性弱点与优点进行艺术的关照与生发。
《历史的天空》写的也是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文革以后,叙述了一组革命者艰难创业、并在创业中磨练和改造人性的血雨腥风的历程——这群人,不论当初带了怎样的动机来到军营,不论何等出身,他们身上都很难摆脱农业文化因素的制约,所以他们的磨练和改造就显得特别困难,惟其如此,闯荡过来的人物无不是“九死一生”,胜利的取得也才来之不易。《天空》的功绩在于它不仅写了敌人的凶残嘴脸,还进一步写到了我军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生与死的较量。先是川陕红军搞肃反、“改造”干部,成立改造班,勒令交代“错误”思想,交不出被说成顽固不化、“自绝于党”,一部分人被杀戮。影响所及——张普景认为梁必达是投机分子、害群之马,对革命绝对有害,不愿对他进行改造,于是视同“情敌”的江古碑之流乘机提出秘密处决他的主张,张赞成,幸好特委杨司令员不同意,反而委以重任。搭档李文彬和他一起工作时心里只想着怎样搞倒他,终而捏造证据,说他“搞山头”“拜把子”,迷信黄道吉日,拜日伪政权维持会会长为干爷……一系列罪名上报分区特委。后来杨司令员遭另人暗算后离开分区,江古碑、李文彬等人代理时政,有了用武之地,首先把免梁必达隔离审查,浑身打得不成人样,只有红颜知己冒险视望。又是杨司令及时赶回来捆押者方得平反。经历此事后梁必达聪明了,变得谦虚恭谨,好动脑筋了——他发现内部的错误更难对付,革命只靠杀人还不行,要有策略。文革时,梁必达又被老对头江古碑整倒,差一点丢掉性命,战友张普景就是死在江的手上,死得荡气回肠。从江一贯的表现可见,他们是一类比敌人还要险恶的家伙,能够长期潜伏在群众中间,一旦得势就跳出来,不择手段地迫害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的人。所以,一个人参加什么组织可以选择,选择的过程充满偶然性,但是好人、坏人不是偶然的。由于它,投靠国民党的陈墨涵能够与共产党人殊途同归,走到一起,与梁必达肝胆相照;由于它,江古碑说起来是同志,一开始就在一条战壕里,最终原形毕露,成为千古罪犯——假文革之名,行迫害之事!英雄们的信念在战时与平时或文革这样的动乱时期大不相同,它是变动的,有的正向变化,有的反其道行之,《历史的天空》描写 “英雄”时,着眼焦点不仅在战争年代,更重要的是在守成时期的和平年代,可谓匠心良苦、意味深长!由此张普景等人的死于动乱、梁大牙等人的九死一生也就具备了深刻的思想认识价值
写人物命运,写人的成功与失败,落脚点都落在人性的弱点与缺陷、人性的优点与圆满上,无论是从梁必达、刘汉英等人身上,还是从陈墨涵、李文彬等人身上,我们都能发现作家对他们各自人性优劣的客观剔析,从而使这两个庞大的政治集团的内部,各自有了各自内在的灵魂——换句话说就是,这两大集团不仅要面对外部的敌人,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内部的各种危险。内忧外患,使这两个集团的较量,最终升华为人格的比试,尽管充满了艰辛,但亦从这复杂的人性的角逐中,显现并弘扬了真正的英雄主义与人格精神。
[注释]
[1]真名论坛 (http://www.zmw.cn/bbs/),蒋泥:谈《历史的天空》与《亮剑》
[2]《中华读书报》,2001年01月03日,张志忠:振翅在《历史的天空》
[3]徐贵祥.《历史的天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8月
[4] 都梁.《亮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551、564页。
[5]都梁.《亮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395-396页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