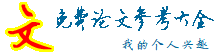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仿佛力之舞围绕一个中心,/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在心中化为乌有。
这首诗中描述的是“在巴黎植物园里所看到的一只铁栏内的豹”,诗人以一种“以心观物”而非“以眼观物”的态度来考察栏中的“英雄”,单从横向组合的语言层面来说,我们能接受到这样一个概括信息:“一只豹在铁栏内被囚禁着,它想冲出眼前的屏障。反复狂躁之后,它终于累了,疲软地要沉沉睡去。”很明显,这点信息距离创作者的真实用意相去甚远。放弃了人类中“英雄”的含义,忽视了诗人所感受理解的时代,我们便不能真正领略他笔底的栏中之豹。从心理机制上来看,这时要求联想的更大程度的投入,从而拓展语言,直抵语言符号背后的真实。换句话说,这时语言符号的意义要求调动潜在的像索绪尔所称的记忆系列,要把不在现场的各要素揉进语言链中加以理解。晏殊留有词句“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尤其是“夕阳西下几时回?”一句,虽问得童稚无理,却反映出感慨岁月匆匆的心理真实。要捕捉到词句的真实内涵或说是词人的心迹,刻板的意象叠加或称是简单地进行语言解码都不会是有效的手段,甚或是一种缘木求鱼而贻笑他人之举。
钱钟书先生在他的《通感》一文中,曾提及到这样几件事,他说宋祁《玉楼春》有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笠翁余集》卷八《窥词管见》第七则别抒己见,加以嘲笑:“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苏轼少作《夜行观星》有一句“小星闹若沸”,纪昀《评点苏轼》卷二在句旁抹一道墨杠子,加批:“似流星”。此两件事中,李渔及纪昀的理解都因为受制于语言要素的横向组合,更多追究了它语法层面的涵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李渔嘲笑宋祁句还是纪昀曲解苏诗,都说明语言符号要传达信息,可以是语法层面的横向组合关系,还可以因为语言环境的存在,而影响到语言符号组合之后的表达结果。就以上面所提及的两件事说来,李渔受制于“闹”字的听觉蕴义,纪昀更科学地追究“沸”般“闹”的小星之物理真实,他们都因为对词句所描绘的真实情景的想象和真切的感受,从而曲解了原意,现代作品之中,如宋祁、苏轼那般的创新语言符号(运用固有的语言个体或语言链来传达一种更高的艺术真实)的尝试很多很多。
顾城说:“有一次,我看到太阳,一下就掠过新鲜、圆、红、早晨等直觉和观念,想到了草莓,于是就产生了这句话:‘太阳是甜的’。”“太阳”与“甜”之间的组合,超出了语义内容和逻辑范畴的制约,摆脱了历史的、社会的约定俗成,从而实现了他特定条件下的心理真实的表现。我称这种违反词语之间的正常搭配规则的组合为语言的纵向关系,从形式上来看,它预示着新的感受的表达,同时也期待着读者的认同与接受,这便是纵深语言组合在表意(情)上的预示与召唤。
胡玫的《夏天,走出我的记忆》:“携着满眼的绿色/沿着叶铺就的清凉/踮起狂躁的脚尖/你悄悄走出我的记忆。”四句诗全是超常搭配,表现诗人旧地重游时回忆起逝去的往事,不由得黯然神伤,心烦意乱,直至恢复了平衡。若是不重视作者的感受直觉,便会认为它们是所谓的病句形式,是一种不合句法结构的组合原则和反正常逻辑的推理。然而,诗歌正是以固有的符号来呈现新的感受直觉,并寄寓于我们所见到的诗人笔底的形式。这形式预设了新颖的情与义。这一特殊语言序列显得荒诞,但作品也就通过它的特殊要素的联系,完成了内蕴潜伏及对解读者的期待。
从上述内容来看,语言的纵向联系性质,开创了语言表现的新天地,它成为现代作家对语言的追求的一种普遍现象,当然也取得很多成功的尝试,甚或成为典范。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符号:语言与艺术》第195页
2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71页
4 转引自何锐、翟大炳著《现代诗技巧与传达》第144页、第207页
6 转引自[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世界史纲》(第十五版),第89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 转引自钱钟书著《七缀集》第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0 转引自《现代诗技巧与传达》第273页,第21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