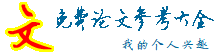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论文导读::“身体写作”使女性在文学史上划下了浓重的一笔,实现了女性对自我的颠覆。身体写作所体现的狂欢性使女性冲出男性主流世界,发出了庞大的女性话语。由于对身体欲望写作理论解构的不彻底性,很容易促使女性文学在展现女性身体欲望的同时陷入尴尬的境地,导致女性文学中身体写作的被误读。
论文关键词:身体写作,女性主义,误读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解放使得女性对自我开始有了重新的认识,沐浴在开放新风中的女性迫不及待地挣脱传统社会对自身的枷锁,对以男性为主的世界提出了挑战,她们开始主张个人的权力与权益。她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在政治、经济、教育方面所享受到的平等权利,而提出了在文化、语言等意识形态所应该拥有的话语权,重塑女性文学史,发出女性自我的声音,而不再是依托男性的视野、男性的话语塑造女性的形象。特别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进入,女性的这种渴望更加明显。女性主义所倡导的揭发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压抑和对文学的垄断,呼吁要走出男性传统的藩篱,强调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的独有性,把绝对的个人经验贯穿于写作实践中,让更多的人倾听女性的声音。于是到了九十年代,林白、陈染、海男等女性作家以抒写女性自我的身体感受而受到文坛上的瞩目。随后的卫慧、安妮宝贝、棉棉等新一代女作家以彻底的放逐自我身体感受,大胆揭示女性身体体验,以身体语言来获得男性世界的话语权。人们惊呼,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时代已经到来,女性开始认识自我的感受,书写身体。肯定者们称:“林白的小说完全按照埃来娜·西苏的所指的‘返归女性躯体写作’理论主旨来操作的《一个人的战争》,其写作的实践结果,又恰好,几乎可以说是完整无缺地使西苏理论预测的后果得以实现。”反对者则认为这只是无精神深度的情绪性宣泄以及消费文化制造出来的文化快餐,与具有大胆革新精神的女性主义无关女性主义,他们更是对身体写作中的“下半身写作”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身体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变异,打上了“中国式”的标签。[1]这种身体写作不过依然是在男性文化世界的一种变异的包装而已,从头至尾中国的女性主义依然走不出男性的目光,不过是亲男权的伪女性主义。那么,当代中国的身体写作是否真的暗合了西苏的身体写作理论?批评家在审视中国的身体写作是否存在误读和误解?本文将结合当代女性身体写作现状对此深入探讨。
一、 “身体写作”现状
中国的身体写作在最初一直都是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羞状态,并且这种身体写作大部分地都是男性作家以男性视野而进行,很难实现女性书写自己的身体感受。直到林白、陈染这一批女性作家的出现,叙述者以女性的目光打量自己,勇敢地书写自己的身体感受甚至是隐秘的自慰和同性恋体验。她们开始了女性书写自身体验的历史,将女性的目光从男性社会转向了女性世界,她们不再是传统文学题材中羞羞答答的女性形象,在她们的笔下女性开始了自我的狂欢。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塑造了一个个女性形象,她们美丽而富有魅力,她们注重自我的内心感受。作者在文本中一次又一次地抒写自己的自我身体体验,那些躲在蚊帐之下的自慰场景,以及与男性之间男女之爱的场景,其目的就在于在作家看来,在强大的男性文化氛围下,女性能够给予自己安慰的是自我的身体,女性能够主宰自己的是自我的身体论文开题报告范例。这或许是一种无奈,但也是对强势男性文化的一种颠覆与突围。女性作家通过自己个人化的写作来实现女性对自我的认同。应该来说,这是女性文学的一大进步。
虽然身体写作刚进入中国时首先由王安忆,铁凝等自如应用,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身体禁忌,而陈染,林白这一阶段开始大篇幅描写性细节,但仍较多较细腻地展现了女性的内部心理,让更多的人通过文字来了解禁闭已久的女性世界,但到了卫慧、棉棉阶段,身体写作就单纯成为了欲望和快感的代名词,卫慧在她的《上海宝贝》中写道:“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务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做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2]”。身体写作不再是女权主义者们唤醒女性自觉,走向独立的斗争手段,而更多的是展示一种时尚性和消费性,在巨额的商业利润下迎合着男性偷窥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掉入了欲望化,商品化的陷阱。
赵柏田在《出生于六十年代》[3]一文中写道:“他们开始有了记忆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70年代的中后期,60年代那种迷幻的激情不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是‘红色年代的遗民’”。何为“红色时代的遗民”?即在她们成长的世界里,激情、理想、正义等等统统成了贬义词,她们拒绝积极向上,宏大而富有集体气息的东西,她们喜欢那种阴暗的、软弱的、暧昧的事物,尤其喜欢那些飘移不定、难以抓住的东西。当中国步入传统伦理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转型阶段时,前卫的女作家们紧紧抓住身体写作这一手段,热烈迎合汹涌而来的个人文化潮流。她们拒绝书写群体文化女性主义,因为它是身心割裂、反身体、视肉体为仇寇的。而身体写作重视个体独立和自由,它以“我存在”为中心来认识世界,它立誓要打破禁欲主义和传统的个性禁锢。这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作家们,叛逆、疯狂,并以超越道德、颠覆传统为快乐。袒露与赤裸是展示自我、突显个性的唯一方式。拿自己的身体开涮拿性爱隐私博取大众的尖叫声是她们乐此不疲的游戏。虽然赢来了大面积的抨击与辱骂,但却丝毫没有减少她们的市场,因为对性爱隐私的纪实性描述登峰造极地揭露了人性最原始的性欲冲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封存了几千年的女性隐私如今毫无保留地晾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吸引众多男性的眼球。
当卫慧、棉棉以高昂的性姿态席卷商业文化市场时,传统观念经历了一场地动山摇的冲击。而几年后,当木子美因“摇滚乐手事件”横空出击,在网络上一夜爆红的时候,她带给人们的震撼比她的前辈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放荡充满挑衅的姿态赤裸裸地挑战着现有的文化道德底线。面对世人的指责与谩骂,她竟毫不以为意地说“她在工作之余‘有着非常人性化的爱好——做爱’”,并且还会频频更换性伴侣,会当着朋友的面与朋友的朋友性交。这种“荡妇”行为如今却光明正大地摆到日常生活层面来供他人欣赏,究竟是对男权社会赤裸裸的挑战还是对男权社会的曲意迎合?当性被当做茶余饭后的话题而整天被挂在嘴边时,莫不是一种心灵残疾与畸形的表现。她赤裸裸地对情欲歌咏,对身体热恋,一味地摒弃身体写作的灵魂,将它置于庸俗的场合成为速食年代的“崇性主义”,实在与刚开始的“身体写作”差之千里。[4]身体写作的精神因素完全被漠视,欲望却如巨浪一浪一浪地打了过来,低俗到人们更愿意用色情文学来称呼它。按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色情影像书刊是社会所规范男性统治女性服从性关系的肉感化、具体化,实际上是两性不平等关系的写实。那些打着“身体写作”旗帜,高喊“性解放”、“张扬个性”口号的女人,自以为是在反抗男权,实质上却是挂羊头卖狗肉。女人的放荡不但不会改变女人的历史,反而还会在男人的虎视眈眈下剥离她最后一丝尊严。女性的身体狂欢写作很容易被误置为对性的狂热崇拜,作者在仅仅追求身体快感的同时很容易导致当今新新人类在都市生活状态瞎精神的缺失。在她们看来,精神家园的寻找成为绝世的反讽,这必然是女性写作中自我的歧途。
二、“身体写作”在中国的误读
“引出内在的你,你将得救。不引出内在的你,留在里面的将会毁灭你”(耶稣《福音书》),西苏认为,女性应该学会书写自己的身体,以身体为载体,在男权话语的既定格局中强占自己的位置。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她阐释了“身体写作”的真正含义:“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的身体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地和逐渐地觉醒,关于一个曾经是畏怯的既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 [5]当她试着去改变男性传统对女性“身体”的支配和表述时,实质是在呈示女性对宇宙、自然、社会、阶级、身体、精神、情感及性等方面深层次包括无意识方面的体验。但当这种理论到达中国时,一些前卫的女作家以及市场和媒介仅仅借用“身体写作”这一名称,把“身体写作”简化为欲望、性和本能的写作,而且仅仅是女性性经验的写作论文开题报告范例。身体写作越来越明显地祛除属于上半身的词汇,如知识、思想、哲理、文化、传统等女性主义,而迈向更加张扬、叛逆和颠覆的“下半身”写作。
我们应认识到,父权制对于女性的统治压迫,是人类历史上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事件,西方女性主义毫无疑问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观察事物的崭新视角,中国女性主义由此出发对中国男权意识的揭示也确实发人深省,但盲目地把女性意识仅仅理解为独特的女性经验,特别是身体经验和性经验,以女性的隐私为武器向男性文化宣战,不但不能赢回她们的身体,反而迎合了男性的欲望,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男性文化心理的圈套。在许多评论家看来,身体写作不能简单地视为生理范畴的“肉体”呈现,而是既受到生理感受及无意识幻象的激励,又受到文明规则的束缚,是一种话语方式,也是一种解构等级森严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文化策略。[6] “肉体必须拉住灵魂的衣角”,如果身体写作拒绝了身体感性以外的一切东西,包括历史、社会、文化等人类共同的经验财富,那么,这样的身体写作最终势必坠入失败的深渊。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