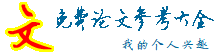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论文导读:它是男性中心社会主导文学的女性意义,也是女性主义文本重新语义话的前本文。然而,不论是男性身份影响着他们对女性的认识与理解,抑或是他们所采取的实际的表现手法,都在事实上依然是妇女成为被描述的对象,审美的客体,男性某种观念,情感的载体,成为没有所指的“空洞能指”,没有话语权的傀儡,因而,女性事实上依然处于沉默。他求婚的方式以及后来对“我”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足以说明他只是想借助“我”来抚平他心中的恐慌,而且只是把“我”当成他的附属物,因为“我”不像吕蓓卡那样有叛逆性格,“我”温顺、贤惠、善良、无知、笨拙,是男权社会淑女标准的典范。而当具有反叛性格的吕蓓卡得知这样一个事实时,她的反映可想而知,发觉自己居然作为一个物品来进行交换和使用,她再也无法忍受而开始了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关键词:女性主义,男权社会,话语权,反抗
一. “疯女人”:作者叛逆的“替身”
女性主义认为:人类的进步和男性的文明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压抑之上的。“一部女性史其实就是女性被压抑、被奴役的历史。父系社会通过亚属国家机器─家庭和婚姻,通过伦理秩序、概念体系等直接、间接的人身强制手段,实行对女性的社会、历史压抑。”[1]这种压抑渗透在父系文明的一切领域,并掩盖、隐匿这一压抑,使女性被排除于历史之外,女性是男性历史的“潜意识”。在历史的长河里,随着父系社会的确立,女性主体地位被男性取代,女性的话语权也随即被剥夺了。男性主体不仅拥有政治、经济、法律等权利,而且拥有“话语权”,“拥有创造密码附会意义之权,有说话权与阐释权”。男性主体作为“统治性群体”, “规定着词义,创造着符号”,操纵着整个语义系统,塑造规定着女性的形象与意义:女性形象无非就是“家庭天使”和“恶妇淫妇”,非此即彼;女性只是男性性爱的对象,是生育的工具和欲望的化身。因此,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中心社会对妇女经济、政治上的控制“已经以性的术语语义化了”,“我们必须把以前构成的性别范畴重新语义话,把意思和意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克服传统上关于女性的联想”。要努力揭示女性之为女性的秘密,以期建立一种全面发展的人的理论。
在语言系统中,女性被讲述被阐释的被动命运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它是男性中心社会主导文学的女性意义,也是女性主义文本重新语义话的前本文。在女性写作出现以前,表现女性的首先是男性作家,女性在作品中的中心地位也首先是男性作家赋予的。许多男性大师真诚关心妇女同情妇女。然而,不论是男性身份影响着他们对女性的认识与理解,抑或是他们所采取的实际的表现手法,都在事实上依然是妇女成为被描述的对象,审美的客体,男性某种观念,情感的载体,成为没有所指的“空洞能指”,没有话语权的傀儡,因而,女性事实上依然处于沉默。在女性书写出现以后,女性成为主人公和叙述人。女性成为话语的主体本身,便是对男性话语专制权威的反叛与否定,它象征性的赋予女性话语权利,从而否定了历史。女性关于女性意义的解释,界定与命名,颠覆了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为物” “为性” “对象化”“客体话”的审美地位,确立了女性的眼光、 女性的视点、女性理解、解释并表达自身及世界的权利。[2]
正是因为女作家们以女性的身份、用女性的语言、站在女性的立场来描写女性体验,女性小说有其独特之处。由于女作家感觉到了父权制的重压,都存在一种“作者身份焦虑”,往往采用“替身”的手法来表现其痛苦愤懑及疯狂,她们的反叛意识投射到小说中的疯女人或魔鬼般的女人身上。“通过将其愤怒和疾病转移到可怕的人物身上,女作家为她们自己和女主角制造了隐秘的替身,以便既遵奉又颠覆父权制文化强加其身的自我定义。所有在小说与诗歌中创造了女魔的19世纪至20世纪的文学妇女,都通过这种女魔来表达其意。从男权观点来看,拒绝在家庭中保持顺从与沉默的妇女都是可怕之物─蛇发妖、海妖、六头怪、蛇身妇及死亡灾星或黑夜女妖。而从女性的视角看来,魔女仅只是一名寻求自我表达的女性。”[3]笔者认为英国著名作家达伏妮•杜穆里埃就是这样一个代表。她在其代表作《蝴蝶梦》中塑造了遵奉父权制文化的女性形象“我”和颠覆父权制文化的女性形象吕蓓卡。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角,对看似从未真正出现过但实际却无处不在的女主人公吕蓓卡进行非传统解读,解构人们对吕蓓卡传统认识。吕蓓卡并非一个十恶不赦、心肠狠毒的坏女人,她只是在用实际行动来对传统的父权制社会提出控诉,她是作者达伏妮.杜穆里埃和主人公“我”叛逆面的“替身”。
二. 被剥夺话语权的吕蓓卡
父权文化一直将妇女排斥在外,传统的叙事手法和阐释话语都是男性的,妇女的语言是“无权的语言”,语言的意义也产生于不同说话主题的社会存在,事实与描述之间的距离由话语权决定,话语权代表政治权,政治权决定了话语权。女性主义认为,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受语言的影响,除非语言允许,我们才能看、听、思考,语言以一种有意义的形式决定思想,限制概念的形式,甚至决定认知结构。由于在语言的创造与解释中女性的缺席和男性的控制性,妇女缺乏自己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无名感是妇女的普遍处境。妇女的体验常常由男性并通过由男性发展的语言媒介记录描述,在男性的话语系统中,女性的体验或者被忽略或者被歪曲。因此,女性批评家们把目光投向了女性写作。在这类作品中,女性作为主人公与叙述人,能用女性的语言来表达女性体验,两个主体融为一体。
《蝴蝶梦》是一部典型的“女性写作”。笔者认为,这部作品某种程度肯定了女性作为话语的主体者,即女性作为叙述者和主人公,以“我”的名义,以“妇女的名义和身份讲述、言说,使女性在幻想的秩序中具有主体——思维主体、 审美主体、 话语主体——的身份,实际上否定了男性话语主体独尊的权威,打破了女性沉默而一任被男性讲述的历史使命”,这无疑是对父系文明历史关于女性规则的重新语义化。但因为受着父权制的重压,整部作品仍然逃脱不掉父权制标准的阴影,所以作者采用了传统的“家庭天使”和“恶妇淫妇”二元对立模式,而且在给予一女主人公“我”话语权的同时,却完全剥夺了另一女主人公的话语权。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