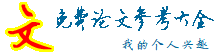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摘要:本文力图对80年来沈从文研究所经历的四个时期(滥觞期、沉寂期、反思重构期、多元开拓期)加以清晰的描述并辅之以客观评价,以为研究者之参考。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研究 80年 综述
沈从文研究不是一个新课题,但其意义却弥久恒新。从1925年5月3日《晨报副刊》发表唯刚(即林宰平)的《大学与学生》一文开始到今天,沈从文研究已经走过足足八十余个春秋。从文先生已于二十年前离开人世,然而他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文学著作以及渊深的思想文化遗产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学人,孜孜以求,乐此不疲地去探索、去开掘。
在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多年里,沈从文研究与其创作几乎同步,不过此时的研究尚处于滥觞期。研究者多就沈从文的某一篇作品发表评论,涉及的往往也只是作品的某些方面,且批评方法简单粗糙,还没有形成系统。此外,因为沈从文在三、四十年代文坛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其特立独行的文学及政治姿态,论者对于沈从文的评价毁誉不一,且贬抑多于褒扬。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中,不少论者还是抓住了沈从文不同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些特质,体现了研究者敏锐的眼光。其中最为人所重视的文章当数苏雪林1934年发表于《文学》第三卷第三期上的《沈从文论》以及刘西渭1935年6月发表于《文学季刊》2卷3期上的《<边城>与<八骏图>》。前者将沈从文已有的短篇小说从题材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并注意到沈从文小说具有题材新鲜、语言真实的特点;而后者则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废名同沈从文两相对照,指出二人在风格上的差异。诸如此类在今天看似微不足道的观点,却是沈从文研究的宝贵财富,它们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步入五十年代以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大陆的沈从文研究基本进入沉寂期。虽然在五十年代的三部中国新文学史(1954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5年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1956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编著者都有论及沈从文,不过此时的沈从文却是以反动文化人的面目出现的。正当整个大陆学术界万马齐喑的六、七十年代,海外汉学家的沈从文研究却薪火相传,蔚为可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藉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英文版初版、1979年中文版)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1984年)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两部文学史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沈从文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一、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确立。虽然,由于编写体例不同,二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二、极力将沈从文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前者认为,在道德意识方面,沈从文“是与华茨华斯、叶慈,社会实践论文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是中国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后者则推举沈从文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犹如莫泊桑之于法国,契诃夫之于俄国。三、作为上述判断的根据,则是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夏志清认为,沈从文肯定了“神话的想象力”是使人类“在现代社会中,唯一能够保全生命完整的力量”。而在司马长风的笔下,无论是对《八骏图》主题的揭示:“无常的人性,无常的爱,无常的欲,这是《八骏图》所写的主题,人一堕无常之纲,便成为奴隶”。还是对相关作品的激赏:“沈从文将整个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心灵的哀欢”(关于《湘行散记》);“……《长河》具有这些,但不止这些,还可以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关于《长河》),都显示出一种对沈从文创作新的切入角度:沈从文对民族、人类人性流变的深层关怀。
八十年代,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在学术领域的逐渐衰落,人们的思想开始解禁。沈从文研究也就不再是一个雷区,而学术界重新解读和评定沈从文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此时的沈从文研究开始步入反思重构期,其主要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凌宇1980年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辑上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可谓开风气之先。文章以相当的篇幅,通过对沈从文20-40年代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卷入的文坛论争的辨析,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而是一个既对历届军阀政府及国民党政府取批判姿态,又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保持距离的民主主义者。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