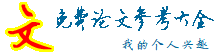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第一种潜在的机制是:宗教信仰影响物质资本积累,从而制约着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认为宗教信仰也许影响了人们节俭方面的价值观,从而改变了储蓄率、资本积累水平以及经济增长。例如,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2003)的研究发现,在把教育孩子节俭当作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方面,天主教和新教要比不信教的人分别高出3.8和2.7个百分点。其他宗教的影响常常是在量值上较大,但却没有统计学意义。
第二种被重视的机制是认为宗教信仰会改变人们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具体而言,宗教通常会影响到不同群体的教育、健康状况。研究表明在个体和家庭的微观层面,经济行为和产出与宗教相关。宗教也许会导向一个更为健康的标准(通过反对一些不良习惯,如吸毒、暴食、赌博、酗酒等),更高的健康水平能够通过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生产力。在一些医学研究中也表明,具有严格宗教的群体看起来享受更长的寿命和更低概率的癌症、中风、心脏病等,因为他们每天都遵循严格与健康相关的活动。一些经济学家观察到具有更高宗教群体的地理区域暴力和非暴力犯罪活动都比较少。而且,特定的宗教似乎能够提高教育水平,如美国犹太人作为基督群体具有显著的更高的工资和收入,主要由于他们具有更高标准的教育。当然,他们在学校教育上也具有很高的回报率(Chiswick, B.,1983、1985)。
第三种可能的影响机制强调了宗教对于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尽管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度量在经济学中并未得到认可,但关于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已较多,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促进信任与合作上。宗教信仰被认为是一种支持经济增长的伦理结构,具有内在伦理驱动机制和内部化伦理指导系统。同时,信仰行为可以作为个体身份与责任的联系和信号设置(Minkler, L., Cosgel, M. 2004)),从而增强了社会资本的积累。甚至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参与宗教教派具有能够潜在地给后代带来两个方面的经济利益(Anderson,1988)。第一个渠道,宗教信仰可以作为一种荣誉信号:使穷人看上去更像潜在的雇员,借贷者和消费者,作为一个好教派的成员能够减少与独特个体交往的风险从而最终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二,教派可以提供超越法律的手段来建立信任而且减少不确定性,改善效率,特别是当公关制约合约很弱时。近来的研究也表明,宗教也许能够增加信任的程度而且可以减少腐败和犯罪行为,增加一个国家对陌生者的开放度从而使得经济越来越对外资和就业者开放。
第四种被重视的机制是宗教通过影响制度起作用。随着经济学对制度因素的重视,从宪法、法律和政策规则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的论著大量出现。但是,对于制度本身的演进则需要从文化和宗教上寻找终极原因。例如,宗教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民主决定因素。罗伯特·巴罗(2004,第52-53页)根据1980年最普遍的宗教国家进行分类后合约,1975—1994年的民主指标平均值为:犹太教0.85(1个国家)、新教0.78(24个国家)、印度教0.66(5个国家)、天主教0.60(49个国家)、佛教0.56(4个国家)、各种东方宗教0.45(3个国家)、其他宗教0.28(17个国家)、穆斯林0.26(32个国家)。这似乎表明,宗教与政治制度及其他制度存在着相关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宗教信仰还同人们的政策偏好以及实际的政策取向有关,如GSZ(2006)的研究了宗教归属对美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不信教的人相比,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答卷人对再分配都持消极态度,虽然有关犹太教徒答卷人的系数没有统计学意义。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更倾向于赞同再分配,尽管其效应在统计上接近于零。
虽然上述几种机制似乎都有道理,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假说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的。正如Hanssmann(2000)所认为的,特定的新教伦理价值观系统产生了系列的劳动投入和经济效率,发源于一种自律、自我克制、勤奋工作和为将来系统计划的伦理。新教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广泛的文化革命。但是,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总是正面的,也有些研究提出了宗教的不利结果。如,宗教也会通过对资本积累、获利、信贷市场和利益等方面的限制而产生负面影响。宗教还会增加用于教堂活动的资源配置从而减少用于自由市场活动的资源投入。暴力活动或公共冲突也许因宗教而减少或增加。一些基本的基督教信念看上去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和世俗经济的价值观和伦理(Beed, C. and Beed, C. ,1996))。
四、包含价值观的合约理论与产权变迁
需要指出的是,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也许在发达国家比较成功,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机制并不明显。特别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物资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并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是近30年来的持续制度变迁。
在传统的增长理论中,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强调了投入生产函数中的要素数量,而新兴的内生增长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然而,这些理论通常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事实抽象之上,忽视了各国之间在制度上的差别(高波、张志鹏,2008)。不幸的是,离开了制度因素,就无法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及其经济绩效,甚至也难以理解工业革命之前那些发达国家的状况。与现在的发达国家相比,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也缺乏可靠的法律保障,资源配置通常受到严重的扭曲。只有通过根本而长期的制度变迁,才能够使投入的生产要素获得更为合理的收益。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解制度变迁提供了大量理论工具和洞见。该理论认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North,D.1991)”具体来说,制度可以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还可以影响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状况,具有改变人们收入水平的重要功能。例如,在市场化转型之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低下,但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足够的激励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就获得了快速增长。
深入研究表明,制度就是对合约安排的选择。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这些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利结构,有时蕴含着权利的直接或间接交换,有时只表明自愿性的或强迫性的约束行为,界定着经济制度的本质。总之,合约是关于产权分配的约定,合约安排的不同对应着相应的产权结构以及背后的政制法律制度,因此,复杂的制度问题都可以抽象成为合约的选择问题。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其中有三类是最常见的,第一类是以资产界定权利,也即是私有产权。第二类是以等级界定权利。第三类是通过法例管制约束竞争。虽然任何社会通常是三类并存的,但总是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竞争也可以受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的约束。
进一步的思考认为,这些约束之间往往是相互配合的,资产界定权利、等级界定权利和法例界定权利,都需要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上的配合与支持。否则单纯的任何一种约束在实施上都会面临非常高的成本。风俗或宗教的认同会降低人们的反对和破坏,也会增加人们实施该合约的动力。对于宗教的这种作用,亚当·斯密(1997,第200页)曾指出过,“早在精于推论和哲理的时代到来之前,宗教,即使还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就已对各种道德准则表示认可期刊网。宗教所引起的恐惧心理可以强迫人们按天然的责任感行事。这对人类的幸福来说太重要了,因而人的天性没有将人类的幸福寄托于缓慢而含糊的哲学研究。”只有在宗教等信仰的协助下,人类才得以建立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开始了经济发展的进程。诺思(1994,第65页)也更为明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单位的成功与意识形态的发展有关,这些意识形态令人信服地将现存所有权结构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合法化了。如果这些结构是在一场广泛的宗教运动中建立的,那是最成功的;统治者与神合为一体(如在法老的埃及)是最令人信服的合法形式。”托尼(2006,第286页)也总结说,“对经济组织合理的评价必须考虑以下事实:如果工业不想因为受伤害的人性不断爆发的反抗使自己瘫痪,它就必须满足并非纯经济的标准。”“古典时代的哲学家划分了自由的职业和奴性的职业;中世纪的哲学家强调财富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财富服务;罗斯金振聋发聩的名言“没有财富,惟有生命”;社会主义者关于组织生产的目的应该是为人民提供服务,而不是为了利润;以上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是试图通过提到一种理想来强调经济活动的工具性质,这种理想则被认为是人类真实本性的表达。”
从人类历史来看,产权安排是多样化且渐进演变的,与此相应在每一种产权安排中,都有形形色色的信念系统作为其组成部分而存在。因为“对于“制度”公平或正义的判断,是每个人的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一部分。(诺思,1994,第48页)”如果我们将每个产权安排中的有关公平合理的伦理判断部分统一称为价值观的话,那么,这种价值观一定要有成体系的信仰或理论来做支持。这是因为,人们并不会随意地遵循某种价值观,他所遵循的价值观总是建立在一定的“解释”或信仰之上,而这些解释和信仰通常能给信仰者带来利益,遵循这些信仰所要求的价值观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正如斯达克和芬克(2004,第112页、122页)所提出的,“宗教是由有关实在的一般解释所构成的,这解释包括跟神灵交换的条件。”“在追求彼世的回报中,人们愿意接受一个延长的交换关系。”显然,宗教通常支持了大部分的价值观合约,同时,意识形态和其他理论学说也能够提供类似功能。所不同的是,宗教为人们提供了彼世或后代的回报,增加了人们遵循特定价值观的收益。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看,个人如何看待游戏规则的公平与公正,明显会影响绩效。价值观和信仰的重要作用在于它有助于降低衡量与实施合约的交易费用。韦伯(2006,第224页)说得更为清楚,他指出,传统这道障碍仅仅靠经济动机是克服不了的。“对于既定生活方式进行任何变革之所以深恶痛绝,就是因为怕天降灾祸。通常在这种反对里面就包含着对经济特权的损害,但是它的效力的大小却要看对于魔法威力的畏惧程度大小而定。”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