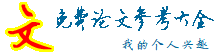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至此,邓巴名字的变化为:邓巴—鲁坦塔—与狼共舞。名字可以界定身份,因为“名字是谁将成为主人的转折点。名字有很多特点,因此一个民族创造属于它自己的名字,始终忠于它们,并让其他民族隶属于它们,从而领导世界上其他民族。”[⑦]苏族名字与狼共舞是苏族与邓巴互相认同身份的象征,也是邓巴自觉混杂的表现。此后苏族人给邓巴一间私人小屋,而邓巴依旧隐瞒白人到来的真相。
随后邓巴开始主动学习苏语,这是邓巴通过语言迈向“混杂体”身份的重要环节。语言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语言承载着文化和历史,人们通过它反省自身并为身份定位,同时“语言更重要的是其生成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尤其凑效于构建独特的团结”[⑧]。从一开始民族本身就构想在语言中,而不是血统中。
邓巴同握拳而立举行印第安式婚礼后,开始穿戴印第安人装束:头戴羽毛、身穿麻布、佩戴装饰。在此,除名字、语言、文化身份混杂外,邓巴开始外表装束混杂。随后邓巴告诉踢鸟,有关白人到来的真相,苏族人决定搬去冬营。邓巴回要塞取日记本混杂,西斯科被当场打死,邓巴被打昏。如果说在殖民语境中“主体之间能够被认作‘他者’的区别,是最直接、快速觉察到的身体和声音的表面区别(肤色,眼睛形状,头发颜色,身体外型,语言,方言或口音)。这些被认为是他们自身不可否认的‘天生’低等标志。”[⑨]那么这里西斯科的死及邓巴的不幸遭遇,则仅仅因其具有“低等标志”的混杂装束:头上一片羽毛、粗制麻布、标志性装饰,遮蔽其军装(小马甲、裤子和靴子)、蓝眼睛、白皮肤。
审判时邓巴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会说英语吗?被踢打的邓巴用英语表明其白人身份。这里显示英语有至上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文化霸权重要的助推器,自认为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的高等语言,也是殖民和权力话语进行思想殖民的锐利武器。殖民时期被殖民者被迫放弃自己的语言而接受英语教育,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不再是承载其文化的语言。
邓巴希冀日记本能证明其身份,却因大字不识的士兵斯必维(Spivey)的私藏无法证实中国论文网。接着邓巴被追问次数最多的问题:他为何不穿军装,而穿成这样(混杂装束)?随后邓巴被当成“叛国者”遭到白人的放逐:包括其身份、历史和语言。在面对是否与美国军队合作以减轻其叛国行为时,邓巴索性自我放逐,选择用苏语应答表明自己印第安身份的立场:我是与狼共舞,我给你们没什么可说的,你们不配给我谈话。这些苏语词语的重量,足以承担邓巴的苏族身份,这触碰了美国军官和士兵满腹的优越感,最终邓巴被判运回海斯堡去面临绞刑。
当荷枪实弹的白人士兵争相枪杀不忍离开邓巴的两只袜子时,伤痕累累的邓巴为解救它而再次受到重击,只能无助地望着两只袜子遭受西斯科的惨剧。苏族解救邓巴时,他亲手杀死斯必维。随后邓巴对此评价为:在河边杀那些士兵是件好事,杀这些人无所谓,我喜欢这样做。至此在对待印第安人与白人战斗的问题上,邓巴从先前对苏族捕杀白人猎手后狂欢的抵触,到这里的认同并亲自作为苏族人血拼白人士兵。如果把邓巴的身份比喻成一个钟摆,两端是白人与印第安人,中间是两者的混杂体,那么此时他的身份停留在印第安人那端的至高点上。
邓巴返回冬营后,决定与握拳而立一起离开苏族。镜头在苏族村民目送他们远去中接近尾声。此时,邓巴的身份再次开始摇摆,因为他要去找那些懂道理的人混杂,而这类人只能是白人,而不是一直被殖民的印第安人。
五、结语
整部影片中邓巴的身份摇摆于“接触区”,处于“文化之间”(culture in -between),逐渐“本土化”(going native)变成“混杂体”。混杂体是“在接触区内由殖民活动引起的新型跨文化形式”,是“通过重复差别对待身份的结果,对假定的殖民身份进行革命”,从而“体现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互相依赖,共同构建主体性”[⑩],使彼此的文化身份进入“第三空间”。邓巴身份的变化,以及建构为混杂体的路线为:听从歪曲印第安人历史的权力话语→“悬置历史,回到事实本身”,重新认识印第安人及其文化→无意识模拟舞蹈,抗击波尼族时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自觉认同苏族名字、语言、服饰、婚礼、文化→选择苏族身份,其推动力是白人对邓巴身份的“他者化”和“放逐”。最后为保护苏族的利益,具有混杂性身份的邓巴与妻子离开村民,沦为影片尾声“在路上的”,美国内部殖民语境中“流散的白人”(diasporic whitness)。
[①]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Studies:The Key Concepts,Routedge,2007,pp.99-100
[②] Robert Stam and Louise Spence, Colonialism, Racism andRepresentation, n Screen,1983, vol.24,no.2,p.4
[③] 印第安语的野牛是tatanka,邓巴发现野牛并通知苏族,因此Loo ten tant与野牛有关。印第安人的名字都与其勇敢事迹有关,得到印第安人认可的白人才会被前者给予真正的印第安名字,如与狼共舞、握拳而立。
[④] 由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提出,帝国话语通过“他者化”创造其“他者”,是被排除在外的或“控制者”通过权力话语创造的,也是殖民话语创造主体的方式,殖民者通过建构他者而建构自我。
[⑤] Philip Leonard, Nationality Between Poststructralism andPostcolonial Theory, Palgrave Macmillan,2005,p.134
[⑥]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Post-colonialStudiesReader,Routedge,2003,p.342
[⑦] Homi K.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Routledge,2000,p.190
[⑧]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Verson,1991,p.133
[⑨] Bill Ashcroft, Gareth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Reader,Routedge,2003,p.321
[⑩]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Studies:The Key Concepts,Routedge,2007,p.108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