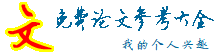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可是,尽管莱拉深受这场家庭悲剧的煎熬,但是她却仍能做到对家的不离不弃,一直留在唐人街,和父母住在一起,给予他们慰藉,为家庭寻找希望。
小说中的她同其他华裔作家笔下的人物一样,经历着由文化困惑造成的种种二元对立:顺从与独立,个人与集体,自由与传统…。一方面,她受到美国主流文化根深蒂固地影响;另一方面,她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中国文化的冲击和社会的歧视,生活在种种矛盾和冲突之中。在家里,中国家庭传统的父母教育与在西方学校里所接受的民主自由思想有着极大的冲突;在社会上,即使在很大程度上已同化成美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但是黄皮肤黑眼睛使得她无法摆脱种族歧视的阴影。这种夹缝式的生存,必然使她经历文化身份困惑、迷失,致使她像所有华裔作家笔下的人物一样常常问自己:“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将归向何方?”。
然而,莱拉却与先前作品中的人物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作为处于文化夹缝中生活的少数族裔,她没有把自身的种种困惑视为不可调和的矛盾体,相反她却利用“第三空间”消解了互不相容的成分,凭借自身两种文化和语言的优势,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媒介,扮演了中西文化之间的翻译者。在学校,她是的教育咨询员,也是翻译员,负责向学校传达移民家庭及其子女的意愿;在家中,她是父母的“传声筒”,成为父母与美国社会之间的交流渠道。在两种巨大的文化差异之下,她不可能成为一个“忠实的译者”,相反她利用语言和双文化背景所赋予自己的优势来过滤,筛选,解释,修正双方的意思,使双方能够彼此接受。(李莉2009)例如,当警察询问安娜自杀的原因时,她清楚以西方警察的思维方式,父母的解释只会徒增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他(警察)根本听不懂,他关心的是那些一般的原因……
我还能给他一个利昂的解释,那就是祖父的遗骨没能安息;或者给他一个妈的解释:安娜觉得自己被出卖了,没有人在他与奥斯瓦尔多的事上能救她,她得承受翁家与梁家梁家生意失败的指责。
但这些我一样也没说.这不是他能写进报告里去的……我只是喃喃地说了一句:这是个说来话长的故事。
正是莱拉运用后殖民主语境下的翻译策略,通过过滤、筛选、删除,才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或至少减弱了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使不能理解变为可理解,使不可言说变为可言说。(陆薇2007:164)正如巴巴所指:原文和译文之间、始源文化(sourceculture)和目的文化(targetculture)之间原本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语言、文化的翻译都是双方协商的结果。翻译过程中有原有意义的丢失,但也有翻译者对它的补充、添加,这些不确定性或是偶然因素,解构了本真意义上的权威性,同时打开了一片解放的可能性。由此可见,作为一名少数族裔,莱拉已经不再是那个对中国文化一味反抗、不顾一切地要与西方文化认同的女孩。她在接受不同文化、运用不同语言的同时,与他们各自保持一定距离,充分利用了这种居间优势,摆脱中国身份或美国身份的纠缠,综合利用这两种文化话语,在东西文化之间保持着对话式的关系。因此,作为东西文化的翻译者,莱拉不仅完成了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定,而且还帮助东西文化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对话。
结语:
作为伍慧明理想中的华裔女性,莱拉文化译者的形象不仅给少数族裔如何解决文化身份问题带来启发,而且也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家们供以效仿。因此,可以说《骨》不仅是一部个人成长小说,而且也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成功之作。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