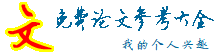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第一,是很多人热议的“汇率陷阱”问题。这包含两个角度,一是美国式货币强权,频频施压于我们要让人民币快速升值。这肯定是不行的,已有日本的前车之鉴。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坚持自己的独立汇率政策和自主安排,是不是就可以简单理解为维持现状?这也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人民币以后要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逐步争取加入世界硬通货俱乐部,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崛起必然、必须的选择。大致是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三大阶段。从目前致力的周边化往前走,最后要走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较充分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如此,才可能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才真正可使人民币最终加入世界硬通货俱乐部并形成我们可得的“铸币税”。所以,在坚持自主的同时,还需把握好正确的汇率机制演进的策略。
第二,是越来越多被人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日益表现出“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行为特点。民生福利的改进,往往滞后于较普遍的期待和不断吊高的胃口,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的增长,又带来越来越强烈的公众知情、参与、监督的民主化、法治化诉求。于是,中国还应该提防南美出现过的“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教训。在网上这么说肯定会引来一片骂声,但作理性的讨论,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没有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得到在深层的机制转换方面做出的支撑,和没有一个从结构优化、节能降耗和有效供给方面对活力的充分提升,这种“福利赶超”误区对我们会有很大的伤害性。一味讲眼前利益而解决福利问题带来的就将是滞胀:一方面工资在增长,物价在推升,另一方面活力和效益跟不上,经济就会停滞下来,最后“福利赶超”也要从云端跌落尘埃。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学术界对它还真有些缩手缩脚。这个事如把话说得很直率,就确实不便去大力宣传,但我觉得学术讨论中,应该力求把它推到政策合理组合的理性框架里。
第三,环境资源的制约。资源、能源、土地等的稀缺性,在发展中必然凸显与强化之后,带来的是资产价格上升、炒作和泡沫问题,并且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我们。最典型的就是现在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我认为当下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如真正要表现出比过去更高的水平,就一定要推进到制度建设框架上。资源的价格、财产的价格、土地的价格、稀缺要素的价格,必然在经济转轨中经历从无价到有价、从低价到高价的演变,在此过程中矛盾重重,新的“价税财联动”的改革与制度建设,是无可回避的,处理得好则大惠民生,处理不好则可能最终大伤民生。
第四,“三农”、“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计划生育等问题与弥合二元经济历史过程。比如,现在的内部讨论中,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和人口大国,计划生育实行三十年之后,已经达到专家预测应有所改变的期限,以后何去何从?我认为应有新的人口政策设计。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必然要与城市化过程和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挑战综合在一起,又迫切需要和弥合二元经济,以及中国必须进一步推进的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形成一个内在协调的、能够长久惠民生的历史发展潮流。这方面的协调把握问题相当复杂,见仁见智。然而管理部门当断需断,这已构成对我们决策力的考验。
第五,我国通盘的产业发展战略还面临着艰难抉择。我很敬重的吴敬琏老师几年前就强调说,要注意去占领“微型曲线”的两端,要争取跨越中国的重化工阶段而走出中国的发展新路。但迄今经济学界正面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几乎没有,为什么呢?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从中央到地方,真正支撑经济增长出现蓬勃局面的还是重化工不论是东南沿海、东北还是内蒙鄂尔多斯这样的地方。如果说我国还不可能简单地超越重化工阶段,我们是不是还要极力追求少走弯路和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中央提出过“新型工业化”这个概念,但怎么样把其操作方案具体化,我个人观察现在的讨论中还是非常模糊的。把新兴产业提升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似乎是把产业发展于新兴领域的方案进一步清晰化的、值得看重的思路。当然,某一新兴产业在全国和在各地方辖区,可能应有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选择,并不是中央规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任何省级行政区都可以全面铺开。这方面需要加强探讨,避免可能出现的误区,争取树立远见卓识。
第六,不可回避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矛盾问题,即中央强调的提高两个比重和社会上热议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中央文件要求在整个收入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和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这个考虑有道理。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