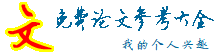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论文导读::侠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是一群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一系列名篇塑造的一个个鲜明的侠客形象,成为后世许多中国人心中流传千古的大侠形象的雏形,而那些女性侠客,更是以双重的性格,非凡的身手,细腻的情感,在文学史上为女性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文关键词:侠客,刺客,双重性格,浪漫主义
一 “侠客”与“刺客”
侠义小说是唐小说中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类别,《聂隐娘》,《红线》,《虬髯客》,《谢小娥传》,《贾人妻》等一系列名篇,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侠客形象,并开后世武侠小说之先河。对于“侠客”的描述,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点出了符合侠士身份必须具备的几个要素:身怀绝技,扶危济困,慷慨潇洒,傲然不羁,也展示出了侠客那种乱世英雄的形象。但是唐小说中关于侠客题材的作品,却很少将其中的侠义精神放大去加以审视,更多的是将其融入复仇,政变,或各种各样的权谋欺诈中去加以塑造,这样就比较容易将其与刺客混为一谈,从而淹没了“侠义”的文化内涵。韩非子曾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从法家的角度,强调了侠的行为的消极因素,例如好武斗勇、目无法纪等,说明侠客是依仗武力与社会秩序抗衡,对他人使用暴力,从这一点来说,侠客与刺客的概念便有些相似之处:侠以维护正义为名,行行刺之实,于是侠客便成了刺客。
唐小说的作者对于侠客行为的描述均有美化之笔,或极力描写其武力之高强,或展示其异于常人的神秘幻术,以转移读者的视线,为其行为制造合理性,但联系时代背景而言,却难以掩饰其刺客的本质。如《甘泽谣》中的《红线》和《传奇》中的《聂隐娘》,专写侠女行盗行刺、参与藩镇之间斗争的故事。表面看来,这些小说展现的是侠客们在政治斗争中的风采,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暗杀之风。以《聂隐娘》为例,《聂隐娘》出自唐裴铏的小说集《传奇》,主人公聂隐娘是魏博大将聂锋之女,自幼由女尼授艺,教以剑术,能白日刺人。后魏博大师派她去行刺政敌——陈许节度使刘昌裔。聂隐娘拜服于刘的睿智与为人,毅然弃暗投明,转为刘昌裔效力,并破了精精儿和妙手空空儿的法术,保护了刘的安全。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中唐后期政局不稳,藩镇割据严重,暗杀之风盛行,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相互残杀,他们彼此以刺客牵制与威慑对方,豢养死士为之效力是必然的事实。而这些被收买,被豢养的,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或出于个人恩怨,或取舍于藩镇势力的强弱,游走于当权者之间,无形中充当了其争权夺利的工具。戈春源认为,“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浪漫主义,为夺取权力,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别与成员进行生死的斗争。他们不惜采用各种阴谋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刺客的出现。”①《聂隐娘》的故事,就反映了这一社会状况,《红线》的故事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刺客和侠客总归有所不同,侠客也许是刺客,但刺客绝不会是侠客,即使二者之间有种种藕断丝连的关系,但历代以来的文人们总会列举出侠客崇高之理由,以区分与那些只是秉承雇主的意志办事,对目标实施谋杀或者暗杀的刺客。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将二者有意识的做了区分,他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初略描述了侠的主要特点,即游侠虽为行侠仗义而杀人,但侠客是有诺必践,为知己者死而不悔的。而刺客并非如此,他们的行为并非出自本身的是非观念,而是秉承雇主的意志办事,受利益的驱动的。陈克标在其《游侠与刺客之辨》一书中,对二者的含义做了现代意义上的解释:“为获得报酬而杀人的就是刺客,因士为知已者死的是游侠;刺客杀人不会心甘情愿以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游侠是不顾自己的安危,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②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唐小说中的“侠客”,便不同于刺客,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蕴含。
二 女侠性格的两面性
“侠”文化由来已久.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侠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自古以来,行侠仗义似乎是男性的专利,侠客的世界就是一个男性的世界。然而唐传奇中却出现了不少女性侠客,身为女性,又是“侠客”,这个双重的身份决定了她们表现出与男性侠客不同的一面,有着明显的双重性格。她们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柔弱,温存,宁静和慈爱,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嫉恶如仇,性格刚烈、甚至称的上心狠手辣的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比如《贾人妻》与《谢小娥传》。
《贾人妻》出自薛用弱的《集异记》论文开题报告范例。讲述了一名女子和唐余千县尉王立相好,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并生有一子,两人感情深厚,相敬如宾,但此女一旦大仇得报,立即抽身而退,并杀掉亲子以斩断情丝。这个形象具有明显的性格冲突:平日里作为一位母亲和妻子,她料理家务,照管生意,对丈夫体贴入微,对孩子慈爱有加,完全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典范。然而这表面上的一切,却是一种掩饰,她的实际身份,却是一个隐藏身份,伺机报仇的女子,一旦大仇得报,她便立即决绝而去,毫无留念之意,为了斩断情缘,她甚至又返回以喂奶的名义杀掉了亲生之子。或许作者是想以此来证明侠女看淡儿女情长的超脱,但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未免心狠手辣,叫人难以接受,这样的侠客可能会受人尊重,但绝谈不上可亲可敬,更谈不上可爱了。作者这种写法显然是出于理想主义,是为了彰显侠客奇特非凡的个性,却以泯灭她身上的“人性”作为代价,未免得不偿失。但这种塑造“侠客”形象的方法却流传下去,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借鉴,后世很多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形象,大多清心寡欲,不食人间烟火,并且性格单一,正所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谢小娥传》讲述的也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女主人公的性格同样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谢小娥和父亲、丈夫及其兄弟僮仆数十人在江上遇盗被“悉沉于江”,财货为盗贼所劫,自己也伤胸折足,其后虽然乞食为生,处境艰难,但她为亲人报仇的信念从未动摇。她女扮男装往返于江上,查访仇人,后来终于找到仇人,并伪装成佣工受雇仇家而伺机报了仇。谢小娥的身份由此呈现出双重性,作为普通而平凡的“估客女”和“商人妻”,作者表现了小娥身为女性的那种柔弱和无助。初见小娥,寻访其遭遇,“小娥呜咽良久”,当作者揭开谜底,她“恸哭再拜”,在仇人申兰家帮佣时,看到自家被劫来的财物,她想起被害死的父亲和丈夫,“未尝不暗泣移时”,这些“呜咽”,“恸哭”,“暗泣”等非常女性化的形容词,给读者这样一种暗示:小娥只是一个遭逢家变,彷徨无助的弱女子,当然这些只是她性格中的一面。而作为一个身怀大仇的女子,她又表现出了远超其年龄的心机和韬略,为报父仇,她一路风餐露宿,沿街乞讨来到亲人遇害之地,女扮男装往返于江上,查访仇人下落,随后又忍辱负重的潜伏在仇人家里伺机报仇,一直到最后终于“抽佩刀,断其首”,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果敢,决绝和无畏与之前那个悲悲切切的弱势女子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一边是女性的柔弱无助,一边是受害者坚毅的复仇,这两种矛盾冲突的行为相结合,便显示出惊人的性格魅力,同时也使谢小娥这个艺术形象更加丰满,这也是《谢小娥传》强于《贾人妻》的地方。
造成女侠形象性格双重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塑造她们这种“中性”性格的人浪漫主义,是一群拥有历史著作权的男性,尽管他们也曾试图探寻女性真正的行动目的和内心的感受,但依然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女性心灵,也就免不了以男性主观的角度,描绘出一群“中性'的超女形象。但无论如何,这些与男性侠客迥然有别的女侠们,以其特立独行的品格和快意恩仇的方式,为唐代文学的女性人物画廊增添了浓浓的色彩。
三 浪漫主义的写作特点
唐小说的写作风格呈现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但是在唐小说中涉及到“侠客”这一主题时,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明显的占了上风。作品除了具有传统作品对人物的具体的现实主义描写之外,更侧重于对他们虚幻的神异性的展示,表现出浓厚的神秘色彩。
唐小说的作者浓墨重彩的展示了侠客们异于凡夫俗子的超人本色。如《甘泽遥》中的侠女红线年仅十九岁,却已身具异术,而且“善弹阮咸,又通经史”,是个文武全才的侠女。《昆仑奴》中的昆仑奴频繁出入戒备森严的显贵后宅,救出红绡后显贵命甲士围捕,“昆仑奴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去向”,烘托出昆仑奴的动作之敏捷,技艺之高超,如果说这些描写还大致不脱出现实主义的描绘,那聂隐娘的形象便已显示出一种仙气,而与常人相去甚远了,她不仅能够化为小虫藏于人腹,化险为夷之后立刻恢复人形,还能“白日刺其人于市”,而“人莫能见”,显得神秘莫测。这些小说中的侠客,或有超人的武艺,或能腾空飞行,更有许多莫测的法术幻术,但归根结底是把侠士形象神化了,这种神乎其神的浪漫主义描写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晚唐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乱世之中的人们处于极度不安之中,无门可入,无可求告,找不到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济世理想难以实现,便把希望寄托到那些具有超现实主义神秘色彩的侠客身上,在想象之中求得一丝安慰,正如郑振铎所言:“一般民众,在受了极端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填塞着不平与愤怨,却又因为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幼稚的心里,乃悬盼着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③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他们通过对侠客快意恩仇形象的刻画,使自己在作品中对抗黑暗的现实,得到精神的胜利。此时,普通人的形象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文人们便展开想象的翅膀,为自己塑造的英雄们添加上普通人不可能具有的神奇本领,让他们在虚幻的世界中去雪不平,除强暴,浪漫主义的描写方法理所当然的占了上风。当然,唐代佛道思想的盛行和民众出于猎奇的心理需要,都对唐小说中“侠客”浪漫主义的描写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戈春源:《刺客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l页
[2]陈克标:《游侠与刺客之辨》,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7期,第33—34页
[3]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二卷《论武侠小说》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4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