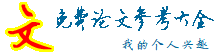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事实上,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也就是“关于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问题,王天根在《史华兹与黄克武:严复思想研究的两条路径》一文中就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是“黄克武著作《自由的所以然》关注现实的价值取向可能导致(的)一些理论预设。”“黄克武认为严复受儒家乐观主义的影响值得商榷。其实,在近代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下,严复的有些作品悲观主义倾向占主体。实际上,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有时主体思想是乐观主义,有时是悲观主义。”[15]虽然王天根的这些质疑并没有涉及到严复自由思想的认识论本质根源问题,但是这种质疑对于黄克武先生的观点无疑具有重要的瓦解作用。
三、问题解决:悲剧意识作为严复的“自由之所以然”
这就接触到第三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严复的自由之所以然?史华茨在《严复与西方》中谈到严复的“不可思议”与斯宾塞的“绝对实在”,而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也将书名改译成《天演论》,这里的“不可思议”、“绝对实在”和“天”究竟意味着什么?按照史华茨的观点,斯宾塞的“绝对实在”乃是一种不可知论的实体预设,它宣告了“人类理性或人类语言克服不可知的绝对不可能”,“斯宾塞在对绝对实在以超然的态度表示敬意之后,又果断地将注意力返视可知领域。”然而斯宾塞的态度“并未削弱严复趋向终极的深深的宗教倾向性”,“对严复来说,‘不可思议’仍然是他获得最后舒适、安慰的根源”[16]。史华茨的这种观点大致是比较合理的,它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话语已经将一种不可认知只能敬畏的“终极实在”存而不论了,由以往对不可知领域的关怀转向仅仅关注可知的领域。这种被自由主义者所遗忘的源于“终极实在”的意识,笔者称之为悲剧意识,它是一种在人类认知理性与理性之外不可认知的神性或必然性之间维持着某种张力的挣扎或斗争,正如古希腊的Mythos(神话)话语言说神意,而哲人在其中思考人生和世界。赫拉克利特说:“一切在地上爬的东西,都是被神的鞭子赶到牧场上去的。”[17]这“神的鞭子”就是人类不可理性认知的“终极实在”(“不可思议”)。而对于这种源于“终极实在”的悲剧意识的遗忘,也注定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必然会失去其深刻性毕业论文范文。严复置身西方传统之外审视自由主义,其背后又有强大的儒家伦理关怀的支撑,因而没有受到这种神性堕落的浸染,所以在他心中保留的正是一种西方人已然无法理解的悲剧精神,而这哲学论文,或许正是构成严复自由观的真正的所以然。
对于“不可思议”,严复在《天演论》“论十:佛法”的按语中直接进行了论述:
“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此则真佛书所谓:‘不可思议’……盖天下事理,如木之分条,水之分派,求解则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在通众异为一同,更进则此所谓同,又成为异,而与他异通于大同。当其可通,皆为可解。如是渐进,至于诸理会归最上之一理,孤立无对,既无不冒,自无与通。无与通则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议也。”[18]
在这里,“无与通”和“不可解”的“不可思议”,既是一种不可知的“本源”,又是“天下事理”的“本源”;它决定“天下事理”的所以然,而人们并不能掌握它,只能以敬畏的心情关注它。诚如孔孟之“命”、老子之“道”或庄子之“羿之彀中”,它是一种必然的命运,又是仁义或自由的当然根源。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儒家才有了它的神圣的天职和使命感,而在老庄的生命情态中也有一种悲剧的情怀。也正是这种基于传统的使命感和悲剧意识,使严复在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表现出一种极大的警惕性。他本能地反对单纯的“个人主义”,因此他讲群己和谐;他糅合了弥尔的消极自由与卢梭的积极自由,而将群己自由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当他发现对他的自由观的某些方面——个人活力的方面,也是斯宾塞的“自我主义”方面——的片面强调可能导致一种强权主义时,他也进行了果断的批评:
“使此说而为感慨有激之言,犹之可也哲学论文,乃至奉为格言,取以律己,将其流极,必使教化退行,一群之中,抵力日增,爱力将息,其为祸害,不可胜谈。”[19]
因此,“不可思议”一语,正足见严复自由之所以然,恰如古希腊那神秘的“唯一者”之于“法律”的所以然[20]。这正是一种悲剧意识,是孔孟“知其不可而强为之”的命运与自由的相对而立,是在“成物”的应然中实现“成己”的目的,而同时在“成己”的努力中追求“成物”的理想,也是庄子那种不忘神圣的必然命运的逍遥与自由。这种悲剧意识也是一种承担意识,承担一种意义、一种责任、一种使命、甚或一种必要的牺牲。而西方自由主义显然已经没有了这种悲剧意识——古希腊城邦与诸神意义上的悲剧意识,他们的自由之所以然,也不是所谓悲观主义的认识论,而是一种寄希望于自由个人联合的群体的理性,是一种没有神性关照的肤浅的乐观主义。当代西方精神世界的失落,或许都与此有关。
参考文献:
[1]刘桂生等.严复思想新论[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5;
[2]刘桂生等.严复思想新论[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3]张汝伦.理解严复[J].读书,1998,(11);
[4][5][6][11][16][美]许华茨.严复与西方[M].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4,212,206,206,88-89;
[7]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1;
[8][9][12][13][14]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166,192,119,30,25;
[10]林同奇.误读与歧见之间——评黄克武对史华茨严复研究的质疑[J].开放时代,2003,(6);
[15]王天根.史华兹与黄克武:严复思想研究的两条路径[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17][20]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3,22;
[18]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80-1381;
[19]严复.有强权无公理此语信欤[J].档案与历史,1990,(3)。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