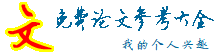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然而,这并不能否定郭沫若所受中国旧诗传统的影响——泰戈尔的诗风清新、冲淡,和中国传统诗风是非常接近的,两者都具有一种东方的古典美,因此很难说《女神》的阴柔之美究竟是来自本民族传统还是来自泰戈尔,本文也并不想仔细分辨,只是用笼统的“传统”一词来代指这种风格的来源。
无论如何,“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女神》中,既显示了诗人古今中外派的广阔诗学视角,也显示了《女神》审美意味的丰富性。忽视这种丰富性,对《女神》的评价是不可能全面的。
《女神》中“太阳”和“月亮”同辉、“壮美”与“静美”共存的现象对于认识中国新诗的缘起及发展也是富有启示性的。“五四”一代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学革命家们,以打破中国传统诗歌束缚为己任,提倡诗体解放,反对模拟因袭,这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然而,这些主张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新诗和传统诗学的割裂以及新诗失范的倾向。1920年11月,时在清华读书的浦薛凤就曾经在《清华周刊》第200期上发表《时髦白话诗底罪恶》一文,对滥做“时髦”白话诗的风气表示了不满。其实,浦薛凤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反对用白话做诗,他也提倡那种“真是诗的白话诗”,只是要反对那种“诗不像诗,文不像文的白话诗”。后来随着新诗的发展,许多诗人认识到了白话新诗泛滥的弊端,于是又转而向中国或西方的传统寻出路,一味在音节的顿挫上下功夫,走上了另一种偏至之途。
这两种倾向的弊端就在于,二者都是孳孳矻矻,仅执于外在形式,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诗之成为诗的核心——诗情诗意诗性。郭沫若创作《女神》时,显然没有蹈入此病。虽然他也力关键词汇,句子既可以长短不拘太阳意象“月亮”意象,又可以严谨规整,类乎古诗。《女神》呈现出一种真正“古今中外派”的姿态,将壮美与优美两种风格融为一炉——当时郭沫若的诗学观念及创作实践,确实已经高出同时代人一筹。
当然,就当时的语境而言,《女神》中壮美、雄浑的“大诗”,更能体现出“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更能体现郭沫若对于新诗发展的意义。当“五四”初期的白话诗人们还不得不为旧诗的羁绊而造成的“解放脚”而感到苦恼的时候,郭沫若却以异军突起之势,写出了那些自由洒脱,气势恢宏的篇章。郭沫若的这类诗作,颇受直白、简单之讥,[12]但却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左翼诗人,这是其在文学史上的主要价值之所在。后来的左翼诗歌因为在向政治的无限迈进之中,逐渐偏离了艺术范畴,使这种壮美风格逐渐式微,这责任显然不能由郭沫若来负。
[①]李闽燕,山东宁阳县人,198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就读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专业。
[②] 张传敏,男,任教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1969年8月出生,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③]本文所引郭沫若《女神》时期诗句,均出自《<女神>及佚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④]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论文格式模板。
[⑤]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⑥]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⑦] 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戴望舒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⑧] 沈从文:《论郭沫若》,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太阳意象“月亮”意象,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⑨] 当然,这也有例外。如郭沫若在《女神》时期的一首佚诗《怨日行》中写到:炎阳何杲杲,晒我山头苗。土崩苗已死,炎阳心正骄。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涛。安得鲁阳戈,挥汝下山椒。这首诗中的太阳,显然不能被视为光明的象征。它是“赤日炎炎似火烧”中的太阳,是“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中的太阳,传统的意味非常强烈。
[⑩] 郭沫若:《论诗通信》,《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11] 郭沫若:《论诗》,郭沫若著、黄淳浩校:《<文艺论集>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页。
[12] 例如苏雪林认为郭沫若的诗“用笔太直率无含蓄不尽之致”(《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湾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90页)。苏雪林以中国传统诗学的“含蓄不尽之致”为标准,来评判具有壮美风格的郭诗,不足为训。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