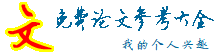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在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期间古罗马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自然灾难。公元79年,古罗马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庞贝,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掩埋,死难人数达1.5万。古罗马散文作家小普林尼记录了他当时真实想法:“我必须承认,给我以安慰的是一种极可怜的想法,就是我确信整个世界会随我一起灭亡古罗马,我仅仅是世界灭亡中一个最微小的生物。”(10)小普林尼还描绘了火山燃烧的状况:“从这里能清晰的看到维苏威火山到处燃烧着熊熊烈火,刺眼的火光在深沉的夜色中显得格外壮观。黎明时分,其他地方的天色应该已经发白,但这里依然笼罩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像是一张硕大无比的黑幔浮在空中,这里充满恐怖和毁灭的黑暗。”(10)在《新约·彼得后书3:16》亦有关于天火销毁世界的叙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The heavens will disappear with a roar),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公元125年,罗马发生大瘟疫夺走了一百万人的生命。公元166年,罗马再次发生瘟疫,每天死亡人数近两千,连当时皇帝也未能幸免。公元250年罗马又一次发生瘟疫,每天约五千人丧生,波及整个罗马,一直持续16年之久。《以赛亚书5:17》这样描绘过上帝惩罚人类的惨状:“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于是,一次次大灾难让罗马人感受到基督教所宣称的世界末日正在逼近。如同惊弓之鸟的罗马人除了皈依上帝、弃恶从善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从古希腊以来,人们就相信灾难与人的善恶相关。苏格拉底曾如是说:“灾难肯定不会降临到好人身上。”(11)
自然灾难同样征服了北方蛮族。从公元前113一直到公元97,图拉真第二次出任执政官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日耳曼人对罗马的威胁远远超过了萨姆尼特人,迦太基人,高卢人乃至帕提亚人。(8)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公元4世纪起,日耳曼大举南侵罗马帝国。丹纳如是描述了北方民族南下的现状和破坏力:“蛮族的洪流也就冲破堤岸,滚滚而来,一批来了又是一批,前后相继……胜迹被摧毁,田园荒芜古罗马,城镇夷为平地……到处是恐惧,愚昧,强暴。来的全是野人,等于于龙人与易洛魁人突然间驻扎在我们这样有文化有思想的社会上。当时的情形有如在宫殿的帐帏桌椅之间放进一群野牛,一群过后又是一群,前面一群留下的残破的东西,再由第二群的铁蹄破坏干净。”(9)然而基督教却借助上帝的鞭子让蛮族屈服了。“在5-7世纪由于蛮族入侵而导致的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破坏了与环境相称的卫生条件结果引发了瘟疫的大流行。……与瘟疫同行的还有灾荒和饥饿,以及一些奇异的天象示警,如彗星、地震等。……面对被毁坏的灿烂辉煌的古典文明遗址,日耳曼民族产生了一种深沉的‘罪孽’意识和发自内心的恐怖感。”(8)正是在这种普遍恐慌和深沉的悔罪氛围中,自然灾难帮助基督教完成了对北方蛮族的驯化。
房龙曾认为基督教的胜利存在某些运气的因素。(5)笔者以为这种运气正是自然灾难帮助基督教走向了统治的宝座。基督教在早期不过是一个简单而弱小的组织,其理论主张未必被人们承认。以其“末日论”为例,如果没有使古罗马人感到极度可怖的“自然杀戮”的不断出现,人们就会认为基督教“末日论”不过是虚妄之谈,也自然不会臣服于这种新的宗教信仰。正是自然灾难通过其不可抗拒的毁灭力使人们相信上帝的绝对存在和绝对权威,人的行为在无处不在的上帝面前必须有所检点。当人们普遍相信上帝存在的时候,基督教所推崇的行为准则必将成为引导人类生命之舟的新指南。相反,古希腊、罗马所奉行的人神同形共性的自由精神就如同深秋的落叶在基督之风的吹袭中挣扎而去。“到了公元五世纪上半叶,克莱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夸张的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他们要再过六百年才能重现光明,在这以前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对待文学艺术,听凭神学家的摆布。”(12)对于基督教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知是克莱斯陀大主教在吹嘘,还是房龙先生说话不严谨,因为单就基督教崇拜唯一的神的精神主张来说它就很难同古典时期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主张脱离干系,更不要说中世纪艺术,如巴西利卡式、拜占庭、罗马式等建筑与古希腊、罗马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写论文。当然,此处的关键不是探讨古典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房龙先生的话来论证基督教在中世纪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事实。
(二)自然灾难粉碎了古希腊、罗马“多神”共存的历史,加速了基督教“一神”独尊时代的来临
在古希腊、罗马的多神崇拜中,无论是以宙斯还是以朱庇特为核心的众神世界都不是引导人们殷殷向善的精神家园。因为神们并未被赋予崇高的道德品质,不像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神是人类道德修养的最高追求。在古希腊、罗马人的视界里,“神虽然比人更强大,更有能力,但人所具有的各种欲望和弱点神都具有,而且往往是一种典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滋生是非,尔虞我诈古罗马,巧取豪夺,偷花摘柳,这一切不光彩的行径在诸神身上屡见不鲜。”(8)从古希腊红绘《诱拐欧罗巴》、威尼斯画派提香的《诱拐欧罗巴》和《达娜厄》可见古希腊众神之主----宙斯在情感方面的放纵和任性。从贝里尼的《众神之宴》、丁托列托的《银河的起源》亦可见到古罗马众神及众神之主朱庇特行为的奢靡和堕落。古希腊、罗马的神明不过是陪同人嬉戏的玩伴,是人们孤独的消遣者;不是使人类行为有所检点的道德守护者,也不是受伤心灵的抚慰者。而与此相反,基督教赋予了上帝绝对的权威、造就万物的伟力和最高的道德标准。《旧约﹒诗篇7:13》这样赞美上帝:“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作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充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旧约﹒诗篇(33:8)》)基督教使人相信恶有恶报。《旧约﹒诗篇7:14》云:“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当然为了更好地吸引信众,基督教也并不把人与神绝对分开,吸纳古希腊、罗马人神关系的一些合理因素,那就是通过耶稣达到人神的统一,顾及了罗马人的传统情感。
当罗马晚期疫疠、地震、水灾等被基督教徒视作上帝惩罚之剑的自然伟力不断发生时,罗马人却不能从满足自己欲望的、与自己本质无异的众神那里获得精神栖居地。而基督徒相信这是上帝对行恶之人的愤怒:“这百姓喜爱妄行,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记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些百姓祈祷好处。……我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旧约﹒耶利米书14:14》)而凡是遵从上帝的人总会得到上帝的荫护:“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不必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旧约﹒诗篇91:14》)这些来自《圣经》的言说在罗马人听来,是上帝对他们的诅咒;自然灾难在罗马人看来,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最终罗马人在自然灾难面前屈服了,也臣服于基督教徒所崇尚的上帝,罗马人按照人的品性所建构的众神世界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了,直到文艺复兴。
(三)自然灾难促使古罗马晚期的人们最终把上帝视作世界之本源。
在古希腊人们已经开始离开万事诸物的表象到神的世界去探索纷繁芜杂世界的本源。苏格拉底相信古罗马,“在事实世界后面,在事物之中,存在一个我们可以发现的秩序。”(13)苏格拉底认为世界之所以有秩序,是因为它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但这种智慧不是个人的,而是神的产物。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创造了井然有序的万物和人。柏拉图对世界的看法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某些观点。他认为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变化和不完善,它依然展现出秩序和目的。”(13)对于是什么使我们所知的世界和宇宙成为可能的问题,柏拉图不得不假定为:“一切事物都有心灵安排,宇宙是世界灵魂在容器中的活动。”(13)柏拉图的宇宙观已经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论相差无几。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中所有变化的最终原因是不动的推动者,(13)虽然他没有将不动的推动者发展成为神学意义上的创造者,但在后来这一思想却被基督教改造为上帝的哲学描述。(13)在希腊哲学家的这套思想基础上,基督教顺理成章地将世界的本源归结于上帝。《旧约﹒耶利米书10:9》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下穹苍。”基督教哲学家普罗丁认定整个世界的终极是“太一”怎么写论文。“太一”是超乎一切的至善,是神,它单纯、唯一,自我规定,是万物的最后根源。
当然,基督教的神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神。黑格尔曾说:“出自拟人主义的希腊神们并没有实际的人类生活,并非既是肉体的而又是精神的神。只有基督教才第一次把这种肉体和精神的现实当作客观存在,表现为神本身的生平事迹,把它引到世界里来。”(2)黑格尔认为基督教的神的客观存“是作为事实发生的,神性或神本身变成肉体,脱胎出世,生活着,忍受着痛苦,死了又从死人中复活起来。这种内容不是由艺术虚构出来的,而是在艺术之外本来就已存在着。”(2)黑格尔对基督教的神的客观存在只作了历史事实的诠释,实际上无助于我们如何理解基督教的神为什么必然要代替古希腊、罗马的神。笔者认为基督教强调的客观存在不仅是神的历史存在,而是神性的客观存在,但是神的历史存在最终是为了证实神性的客观存在。因为“精神并不是作为一种意义,不是在于作为内部的存面,而是在于作为现实的‘真实的东西’。”(14)神性的客观存在是指它的令人恐惧的超人伟力,表现为地震、瘟疫、洪水等自然灾难。对于基督教来说古罗马,自然灾难是上帝手中的军队、警察和监狱,上帝用它们惩罚那些罪恶的人们。从《圣经》可知基督教神的毁灭能为就表现与自然灾难的发生。《旧约·创世纪6:13》就记载了上帝用洪水剪灭人类的故事:“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旧约·创世纪8:5》描述了上帝惩罚人类的惨状:“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淹没了。……凡是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可见,基督教所表现的神性是客观存在的,它表现为创造天地万物的能力和毁灭天地万物的能力。天地万物的生和毁灭又对人类道德的善与恶相关。自然灾难的威力如此巨大,谁还愿意得罪上帝呢?谁敢不敬奉上帝呢?而古希腊、罗马之神虽然在某些方面超人性的个别特征,但它始终不能摆脱作为人的缺陷的存在,如宙斯、朱庇特。在本质上说古希腊、罗马的神性就体现为人性,这种人与神的对等关系恰恰是古典宗教信仰走向解体的根源,因为当基督教把自然灾难与人性的善恶联系在一起进行道德评判时,古典时期那些为所欲为的众神们最终沦为庶人,罗马人所神往的精神家园轰然坍塌。除了上帝之外,古典时期的神们再也没有理由成为承载人类生命之方舟了。
四、结语
上述可知,自然灾难无疑在基督教崛起并逐渐走向意识形态宝座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代替的媒介作用,是它成就了基督教。基督教如果没有抓住自然灾难这个救命稻草的话,古希腊、罗马诸神就很难被取而代之,中世纪的艺术史就可能被改写,所呈现的艺术特征必然是另一番景象。
参考文献:
[1]雅克·德比奇,让·弗兰索瓦,等.西方艺术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70,71
[2](德)黑格尔.朱光潜译.美学(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68,256,255
[3]Rogeo Hanoane John Scheid.罗马人[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15,22,27
[4](英)韦尔斯,世界简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253
[5](美)亨德里克·房龙.人类的故事[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129,135
[6]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7]米海伊尔·里夫希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84
[8]赵林.西方宗教文化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40, 197-198, 200, 54
[9](法)丹纳.艺术哲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1
[10](罗马)小普林尼.维苏威火山的喷发[J].文史2008,(6): P62-64
[11](美)理查得·加纳罗.艺术:让人成为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99
[12](美)亨德里克·房龙.宽容[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5
[13](美)撒穆尔·伊诺夫·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5:56,100,102,102,123
[1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93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