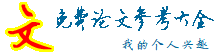| [6]
不难发现,“我”以前是酒楼一石居的老熟客,但现在一切都物是人非,完全成了生客。这也并不妨碍“我”继续坐下来叫上一点小菜和小酒,打发自己的孤独,而不愿意有什么其余的客人上来。我们再来看看,吕纬甫的出场。
这回定是酒客了,因为听得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约略料他走完了楼梯的时候,我便害怕似的抬头去看这无干的同伴,同时也就吃惊的站起来。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P176-177)
鲁迅的小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简笔描写却很有画面感。“我”靠着里面的窗户,正对着楼梯坐着,来往的人群和窗外的风景尽收眼底。步子很缓,说明这位酒客比较稳重、不冒失,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出吕纬甫读书人的身份。“我”的一系列心理变化过程也是值得注意的,“害怕似的”——“吃惊的”——“竟不料”,先是害怕一个人安静的孤独被“无干的同伴”打破,再就是惊讶遇到很久之前的老朋友。“我”的惊讶,可能不只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遇见吕纬甫,更是惊讶吕纬甫经过世事风霜的神态和气质。无非是无聊,吕纬甫也走进了酒楼。
酒楼这个相对封闭和安静的空间,自然成了老友喝酒叙旧的好场所,自然也会再添些酒和下酒菜。在酒精[7]的刺激下,吕纬甫从最开始的踌躇,渐渐向“我”袒露心扉。依此,酒楼为“说/被说”叙事模式的开启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将客观事情的讲述转化为对“灵魂的深”的探寻。这样的探寻,在这样的空间里有了支点和落脚点。按理说,“我”和吕纬甫有十年未见,相见开始颇有些尴尬,但话匣子打开之后,年少时的同窗情谊、教员时代的同事之交定有不少可谈的。然而,鲁迅偏偏让吕纬甫讲了两件颇为无聊、而又和“我”无甚关系的事情来讲,用意何在呢?
参考文献:
[1]王富仁:《时间·空间·人》(四),《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4期.
[2]董晓烨:《文学空间与空间叙事理论》,《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
[3]杨泽编:《阅读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